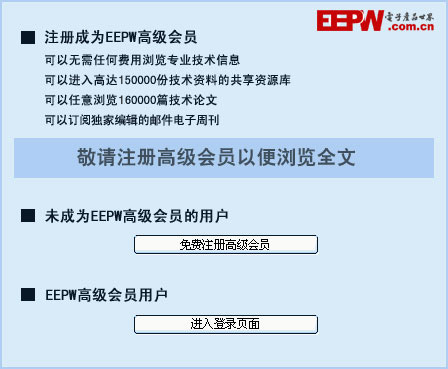ASML,站上十字路口
ASML即将上任的首席执行官Christophe Fouquet面临的最大挑战将是带领公司进入一个新时代,救火员工程文化必须改变。
Martin van den Brink和Peter Wennink在几个月后将离开,这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他们在 ASML 共同占据了十多年的最高职位。Van den Brink 负责开发,不断追求最新技术来满足客户的需求。联合首席执行官温尼克负责财务并担任公司的外交官。他还关心他的员工,从工厂车间到高层。
2024 年和 4 月具有象征意义:届时ASML 成立四十周年。Van den Brink 在 ASML 分拆前不久被飞利浦聘用,他的整个职业生涯都在这家光刻公司度过。由于他领导技术开发的方式,ASML 上升到了平流层的高度。如今,世界上没有一家公司具有可比的市场地位和(目前)令人印象深刻的技术领先地位。很难想象 ASML 在可预见的未来必须将这一地位让给竞争对手。
世界竞争的影响
ASML 的影响不仅限于金融市场和信息技术的经济意义。该公司的战略重要性上升,引起了政界人士的关注。它将荷兰和欧洲置于聚光灯下,并为布鲁塞尔的荷兰政客提供了讨价还价的筹码。来自维尔德霍芬的超级大国也一直是推动荷兰南部布雷恩波特后起之秀的主力。这个高科技地区现在与鹿特丹港的经济和政治重要性以及荷兰在贸易和服务方面的传统优势相匹配。这是由历史学家来决定的,
但就我而言,Martin van den Brink因此完成了比Anton 和Gerard Philips加起来还要伟大的壮举。
2024 年也标志着十多年来强劲增长的结束。上个季度的业绩表明,ASML 并不像想象的那样能够抵御经济衰退。增长正在趋于平稳。因此,Van den Brink 和 Wennink 的告别也标志着 ASML 看似势不可挡、实际上创造了奇迹的时期的结束。该公司推出并运行了一项领先专家曾公开表示怀疑的技术。
未来几十年
现在的问题是未来几十年会带来什么。迄今为止,ASML大约经历了四个时代。最初的八年,直到 1992 年左右,都是为了生存。在此期间,ASML 未能推出 PAS 2500 等独特产品。飞利浦当时提供资金来维持其子公司的运营。
凭借 Van den Brink 领导下开发的高度模块化机器 PAS 5500,ASML 开始占领市场份额。这使它与世纪之交的佳能和尼康处于同一水平。之后,第二期结束。
道格·邓恩(Doug Dunn)的到来开启了ASML的职业化时代。通过收购 SVG,ASML 成为了一个大公司,并开始寻找像 Masktool 和 Brion 这样的公司来加强其技术组合。该公司开始投资整体方法、一套软件和计量硬件,以使其光刻机更加有效。1999 年被任命为首席财务官后,Wennink 立即启动了财务部门的大幅扩张。一些老前辈开始对此不以为然,但后来的动荡增长证明他们错了。
下一代
世纪之交也标志着极紫外光刻技术被选择作为下一代光刻技术(NGL)。正式地,当时离子(ions)或电子(electrons)也被考虑用于 NGL 芯片生产,但从未认真对待。范登布林克 (Van den Brink) 具有战略洞察力,认为光学技术是必由之路。
几年后,157nm 光刻被抛弃,取而代之的是浸没式光刻,即 193nm 的延伸,在透镜和晶圆之间有一层水膜。事实证明,193 纳米工具箱的扩展极大地延长了该技术的寿命。开发光学器件和无差错成像过程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 2006 年之后,水辅助成像获得了发展并开始产生可观的利润。
除了良好的盈利能力之外,沉浸式技术与改进的对准、吞吐量和整体技术相结合,使芯片制造商能够在 EUV 难以成熟时继续扩大规模。该行业必须采用昂贵的多重图案工艺来维持摩尔定律,但它确实有效。多重图案将销售额和市场份额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水平。
即将成年
第三阶段随着 EUV 的成熟而结束。2018 年左右,苹果和台积电决定冒险一试:他们将使用 EUV 制造下一代 iPhone 芯片。Veldhoven 大楼里充满了兴奋:我们将向台湾运送二十台设备!
通过占据技术领先地位,ASML 免受经济衰退的影响。芯片制造商不能忽视 Veldhoven 的机器。那些落后的人付出了代价。典型的例子:英特尔将技术领先地位拱手让给台积电。
第四时期,EUV成为成熟技术。高数值孔径的情况大致相同——我尽量保持简短。
人生第五阶段
ASML生命的第五阶段我们可以期待什么?该公司声称 Christophe Fouquet 也将接替 Van den Brink 的职责,但这似乎不太可能。过去四十年来一直掌握技术统治地位的人的职责很可能会落到一群人身上。ASML 拥有大量可以胜任这项工作的人才,但很难追随 Van den Brink 的地位和声誉。通过不将这些人置于聚光灯下,ASML 使他们免于被与那些被认为不可能成功的人进行比较的负担。
另一方面,值得争论的是 ASML 是否需要另一个 Van den Brink。他在任期间的特点是对芯片尺寸的不懈追求,无论你从哪个角度来看,在未来十年,也许十五年里,我们都会看到这种强大的机制走向终结。这就需要一种不同类型的领导者,一个能够巩固 ASML 在新市场动态中的地位的领导者。
微妙的转变
在分析师会议和季度业绩等公开露面中,ASML 对摩尔定律的叙述已经发生了变化。它越来越少地涉及提高芯片的性能,而越来越多地涉及先进由这些芯片构建的系统。这有点难以解释——这是未来领导层面临的挑战之一。
作为近乎垄断者,下一代 EUV 机器(High NA)或即将推出的变体(Hyper NA)是否会结束收缩,不会产生太大影响。诚然,费尔德霍芬和世界各地的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和工程师都渴望制造出终极的光刻机,但最终,经济规律将决定需要哪些机器。ASML 将非常怀念这位擅长分析并支持此类决策的人。
可靠性
这给我们带来了即将上任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Christophe Fouquet 面临的挑战。他的首要任务将是确保芯片制造商能够从ASML的机器中获取尽可能高的利润。这意味着更高的可靠性和良率。传统上,由于芯片代代的快速更新和 Van den Brink 对技术的关注,前者并不是重中之重。
可靠性仍然不是普通 ASML 工程师的词汇。每台离开 Veldhoven 的机器都是不同的,需要改变。ASML 很清楚这一点。近年来,它开始更加关注可预测性、配置管理和产品生命周期管理。
众所周知,Van den Brink本质上不喜欢这种“无聊”的过程。因此,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它们都不是公司 DNA 的一部分。然而,始终把下一台机器及时准备好作为首要任务是正确的。尼康确实优先考虑可靠性,但在市场上失败了。
但时代在变。随着技术达到极限,游戏规则也会发生变化。ASML 已经开始增强其市场弹性。凭借其高效的 DUV 机器,它为尼康和佳能留下了很小的回旋余地。为了让客户满意,Veldhoven 还必须开始提供同样可靠和高效的 EUV 机器——停机的代价极其高昂。
首要任务是什么?
然而,对于 Fouquet 和他的团队来说,将发明机器和工程驱动的组织转变为流程至上的公司并不容易。这将带来更多的官僚主义。
顽固的开发人员将不得不习惯这一点,但 Fouquet 可以通过论证 ASML 的机器越可靠、生产力越高,他们可以享受的新一代机器的空间就越大来吸引他的工程师。大致意思是“如果你们做得好,Hyper NA将是一个选择;如果你们做得很好,那么hyper-NA将是一个选择;如果事情不可靠,我们将被迫集中所有精力来排除 EUV 和高数值孔径的故障。”
上周,我听到一位分析师声称多重图案 EUV 可能比单次曝光高数值孔径更便宜。因此,维尔德霍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车床(Lathes)
工程挑战目前还没有消失。即使是历史悠久的车床也继续被使用和改进。如果没有其他光刻技术出现可以持续加速信息技术的发展,光学和 EUV 光刻将持续数十年,而 ASML 将能够主导创新的步伐。
Fouquet 和他的团队必须参与一场复杂的游戏,以确保他们的组织不会变得更加傲慢和自满。当蒂埃里·布雷顿(Thierry Breton)或未来的荷兰首相打电话时,他还必须接电话。
进入法国人统领的时代
ASML 已经有一位法国人负责,他希望为客户提供更可预测、更可靠的产品。埃里克·莫里斯(Eric Meurice)上任后不久,在与不满意的客户交谈后,他敦促他的工程师改变路线。在他的第二个任期中,他试图成立一个部门,以确保芯片制造商能够获得与他们一个月前安装的扫描仪完全相同的机器。但这类事情并不是Van den Brink和他的团队的首要任务。他们需要所有资源来启动和运行新技术。
Meurice说得对,但他勉强调整了ASML工程师的态度。也许他只是走在时代的前面。不管怎样,莫里斯未能让 D&E(开发与工程)支持他的工业化倡议。
到现在,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如果 ASML 无法赶上可预测性和可靠性,半导体行业将开始抗议。如果这一举措确实成功,该公司本身将成为主要受益者——它正在采用一种分享客户收入的商业模式。
从这方面来说,Van den Brink的离开恰逢其时。几乎不可能夸大他对 ASML 的重要性,但现在需要一套不同的优先事项。挑战有很多,但尽快将下一代扫描仪推向市场并不是其中之一。ASML 的 D&E 2.0 需要更多的结构、更少的项目、更多的流程。这只有在新领导下才能实现。
由此,我们可以预见ASML的本质将在未来十年发生深刻的变化。毕竟,Van den Brink 领导的 D&E 组织是公司的核心。不仅 Van den Brink 的离开,还有数百名员工(他们将在未来几年退休)的离开,都将从根本上改变 ASML 的创新机器。我们谈论的是那些男人——抱歉,他们几乎都是男人——他们总是准备好扑灭熊熊的大火,即使是在晚上,在世界的另一边。
这种消防员文化将转变为更加官僚化的组织,其中优先考虑可预测性和可靠性。我们谈论的是一家公司,员工习惯于赚取远远高于周围公司同事的薪水。在这样的组织中,潜藏着傲慢和政治——20世纪70年代及以后的飞利浦就是一个著名的例子。也许这就是Fouquet面临的最大挑战:在一家跨国公司中确保胜利者的心态,二十年来,第一的位置一直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Fouquet必须为这家顶级公司带来变革,而他本人已经在这家公司工作了 15 年。这有好处,因为他了解DNA。另一方面,他必须改变根深蒂固的模式,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不会放过任何人,包括他自己。
来源:半导体行业观察
*博客内容为网友个人发布,仅代表博主个人观点,如有侵权请联系工作人员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