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指中国大学被利益扭曲致灵魂丧失理想透支
王长乐教授在《周末评论》所发文章《大学师生关系异化源于制度理性缺失》,对中国大学存在的问题进行了一种全新阐释,认为制度理性的缺失是大学问题之源。笔者完全同意王教授文中所列事实,但是王教授给出的病因笔者有不同看法。理性可以分为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任何制度的出台都是人类理性选择的结果。王教授所指的理性缺失,应该是指价值理性的缺失,如果我的分析没有错,那么构成中国大学的制度理性应该是工具理性,对于工具理性,中国大学不是缺少,而是太多了、太理性了。工具理性在日常生活中的最粗浅的表达就是“可计算性”,由此观之,中国大学的计算本领已经让世人叹为观止,瞠目结舌了。
中国的大学到底怎么了?对此可以初步诊断为,内在的信仰与外在的承认相分离,导致大学灵魂的丧失。
由于中国的大学基本上都是国立大学,这就决定了它的经济来源完全依赖于国家,再加上没有适当的法律保障这种投入的神圣不可侵犯性,注定了大学缺少思想独立性的前提条件,由此,大学内在的价值理性在窘迫中早已遗失。为了获得相对稳定的财政支持,大学被迫蜕变为一个符合计算性要求的变相的准政府机构。在这种艰难的选择面前,大学何为?是把自身定位为一所思想独立的大学还是一个官僚机构?如果想成为思想高地,又担心来自经济方面的隐忧;如果把大学完全定位为一个准政府机构,又与公众早已接受与认同的大学理念相矛盾。在这种基础性的两难困境面前,大学别无选择,只能首鼠两端,见风使舵,或者干脆以牺牲思想独立性为代价,在市场机制的操作空间内向权力投降,退化为精神的侏儒,完全按照官僚机构的模式构建与运作。这不仅是中国面临的现实,也是世界各国都遭遇的局面。这种情况在我国尤其严重,看看时下大学的权力/利益分配地图,所谓的“985”、“211”高校,无不是规训大学独立性的手段。真正的科学进步与这些分类称号有直接的关系吗?目前正在火热进行的教学评估以及重点学科的评审,只不过是规训大学的技术手段进一步具体化和强化而已,这些还只是对机构的宏观控制。对主体的规训则可以通过各种称号的授予来达到,这些称号背后都暗许了利益的承诺。从宏观的分类到微观各种称号的授予,整个大学的独立空间基本丧失殆尽,而所有这些规训都是通过工具理性的可计算性原则与利益的空间分配原则完成的,在这样密布的规训措施的渗透之下,任何机构和主体都无处可逃。中国大学之所以媚俗与没有理想,原因皆在于此。
按世界平均水平,教育投入应该占本国GDP的4%以上(发达国家已达6%),而我国自2002年达到历史高点的3.41%以来,逐年下降,到2005年更是创下近年新低,仅为2.16%,2003年我们的投入是3.28%,而同期的印度是5%,在这种大环境下,艰难度日的大学如何还敢拒绝市场召唤?不要说国家没有钱,近几年财政收入年增长率都在两位数以上,每年的审计报告都能发现各级政府机构浪费数百亿元的现实。这一切导致当下的中国大学出现了一种分裂型“人格”:心比天高,命比纸薄。作为教育的承载者的大学如何摆脱这些困境?我们看到了大学在利益面前的媚笑:向各类明星、权贵笑脸敞开大门;看到了学校合法地向各级政府官员兜售文凭;看到了大学在角落里梦想着提高学费的算计等等。所有这些都使大学演变为一个个戴着耀眼头衔的商业公司。学生与学校的关系迅速退化为一种合同制的产品制造过程。
梅贻琦先生曾谆谆告诫: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只是一个很生动的表面隐喻而已,仅有这两点是远远不够的,也许大学更需要骨气和自由。不过由此引发了大学存在的另一种尴尬:我们的大学多了,学生多了,相对于西南联大来说办学条件也好多了,然而却一直没有培养出多少大师的原因何在?这是一个大问题,目前还没有办法达成共识,但是,至少在微观层面,现在的大学老师都不喜欢上课,却是不争的事实。按说,上课是老师的基本职责所在,也是基本的谋生之道,为何今天的老师不乐于上课呢?原因在于给学生上课是极不经济的行为,课时费被层层剥皮,真正到一线教师手里已经所剩无几了。而且,现在的考评体制也存在严重问题,各高校都注重所谓的科研,反而把本应被关注的教学忽视了,出现了完全本末倒置的怪现象。虽然各个学校也出台一些硬性要求,但效果如何大家心知肚明,这也怪不得老师们,毕竟每个人都要生存。在目前的考评体制下,课上得再好,对于个人目标的实现也是于事无补的,这就从根本上动摇了大学知识传播链条的完整性,甭说不出大师,在这种模式下能够培养出合格的“产品”已经是教与学双方的最大努力空间了。(作者李侠为中南大学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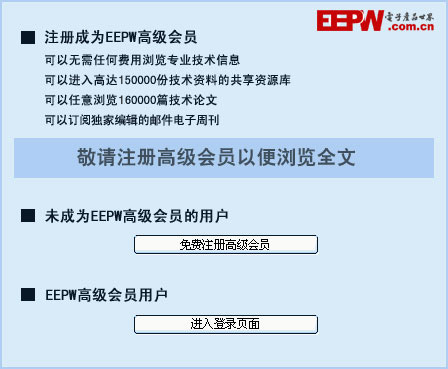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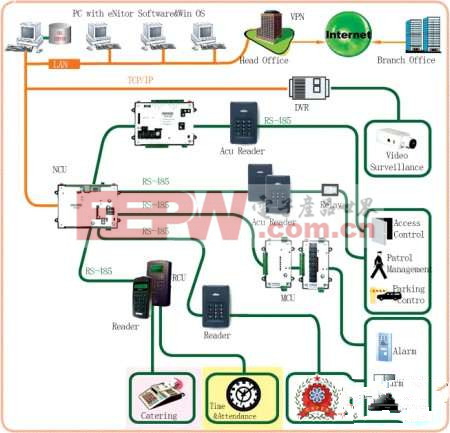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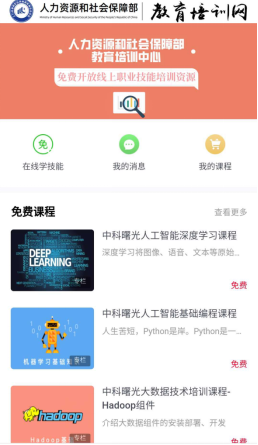


评论